那时候,我有一个好朋友,叫小舟。我们是同桌,是饭搭子,是放学后能一起在操场上晃荡到天黑,有说不完废话的人。我们都喜欢唱歌,都有一点在那个年纪看来不合时宜的文艺腔。我们约好了,要在高三那年的元旦晚会上,合唱这首歌。
为了这个约定,我们准备了很久。下午自习课后的空闲时间,躲在没什么人的音乐教室里,一遍遍地练。他唱主歌,我和声;我唱副歌,他给我垫音。哪个地方的换气要一致,哪个字的尾音要拖长,我们都抠得仔仔细细。窗外的梧桐树叶从绿变黄,再到落光,我们俩的声音,就在那间空旷的教室里,慢慢地、笨拙地、却又无比真诚地缠绕在一起。唱到“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,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”时,我们会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,然后一起笑场,觉得这歌词太沉重了,离我们十七岁的生活太遥远了。那时候以为,身边的人,会像这首歌的旋律一样,永远定格在那个美好的和弦里,不会改变。
后来,晚会如愿举行了。我们穿着白衬衫,站在闪烁的彩灯下,台下是黑压压的同学和老师。音乐响起,我开口唱出第一句,能听到自己声音里因为紧张而带着的微微颤抖。但当我侧过头,看到小舟也正看向我,眼神里是同样的紧张和鼓励时,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下来。那四分多钟,像一场短暂而绚烂的梦。我们的声音在麦克风里混合,飘荡在礼堂上空,台下掌声雷动。那一刻,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唱完了一首歌,更像是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,一个关于友谊、关于青春、关于某种不言而喻的承诺的仪式。
大学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,一南一北。刚开始,联系还很频繁。在电话里,我们还会提起那次演出,互相调侃对方当时哪个地方差点破音。第一个寒假回家,高中同学聚会,大家在KTV里起哄,非要我们再唱一遍《一生有你》。我们拿着话筒,相视一笑,前奏响起,很自然地就接了上去。声音不如当年清亮了,气息也有些跟不上了,可那种默契还在。唱完了,大家鼓掌,有人感叹:“你俩这配合,绝了!”我们碰了碰杯,杯子里是冒着泡的啤酒,心里是暖融融的得意。那时候觉得,距离不是问题,这首歌,我们会一直唱下去。
可是,时间这东西,它不说话,却悄悄地改变着一切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的联系变少了。从每天发信息,到每周打个电话,再到后来,只是在朋友圈里互相点个赞。他的动态里,出现了我不认识的新朋友,参与了我不了解的项目;我的生活里,也充满了学业、实习和新的社交圈。我们偶尔通话,话题也从过去的回忆、共同的熟人,慢慢变成了对未来的迷茫、对现实的抱怨。语气里,少了那份毫无顾忌的分享,多了一丝小心翼翼的客套。
有一次,我给他打电话,兴致勃勃地说起工作中遇到的一件趣事,说到一半,他那边忽然沉默了一下,然后说:“哦,这样啊,我不太懂你们这个领域。”那一刻,我所有想说的话,都卡在了喉咙里。我忽然意识到,我们之间,已经横亘了一条看不见的鸿沟。我们不再是在同一间教室里,对着同一本习题册发愁的少年了。我们走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,看着不同的风景,奔向不同的远方。
那感觉,就像一首曾经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二重唱,一个人还在原来的调上,另一个人,却已经悄悄转了Key。声音还是那两个声音,但合在一起,就是不和谐了,刺耳了。
最后一次听到他提起那首歌,是在一次微信聊天里。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啥时候有空,再合作一把《一生有你》啊?”他回了一个笑哭的表情,然后说:“哎,算了,早忘了怎么唱了。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,现在哪儿还唱得出来那种感觉。”
“早忘了怎么唱了。”
“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。”
我看着屏幕上那行字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,空落落地疼。我知道,他不是真的忘了那旋律,他是忘了,或者说,是主动告别了唱那首歌时的心情,以及歌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时代。
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唱《一生有你》了。
一个人开车的时候,电台里如果偶然飘出那段熟悉的前奏,我会像被烫到一样,立刻伸手换台。在KTV里,哪怕有人点了,我也只是默默地听着,当旋律行进到我们曾经配合最默契的那段和声时,我会下意识地屏住呼吸,仿佛一开口,就会惊扰了沉睡在时光里的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不是歌词写得不对,也不是旋律不好听了。恰恰相反,是它太对了,对得让人心碎。它精准地预言了我们后来的一切——“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,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”。它像一个青春的预言家,而我们,成了那个预言落空的反面证明。
这首歌,像一把钥匙,一把太过精确的钥匙。它能打开一扇门,那扇门后面,是下午三点的阳光,是音乐教室的木质地板味,是少年清澈的眼神和汗湿的手心,是掌声,是梦想,是那种以为“一生”真的可以很轻易说出口的笃定。门后的世界太美好了,美好得像一个易碎的琉璃盏。而我,已经没有勇气再推开那扇门了。我怕走进去,就被那过于浓烈的过往包围,无法呼吸;我更怕走出来时,面对眼前现实的空旷,会更加失落。
它不再仅仅是一首歌,它是我整个青春时代的一个注脚,一个缩影,一个盛放着所有纯粹、热烈、毫无保留的情感的容器。唱它,需要调动起那个时代的全部自己。可那个自己,已经留在那间礼堂的舞台上了。现在的我,嗓音里沾了世故的尘埃,心境里藏了权衡的计较,我唱不出那种味道了。强行去唱,像是一种装潢,对过去,也对现在。
所以,就让它留在那里吧。
留在那个MP3还很珍贵的年代,留在那条跑道上画着白线的操场,留在那两个穿着白衬衫、以为唱完这首歌就能拥有全世界的少年那里。
歌,还是那首歌。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,已经走散了。有些歌,之所以不敢再唱,是因为它连接的不是一个旋律,一段歌词,而是整整一段人生。那段人生太好了,好到你不忍心用现在的任何一点东西去打扰它,包括你已然变化的声音。
它就安静地待在我的歌单最深处,像一个上了锁的盒子。我知道它在,就够了。偶尔,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深夜,它的旋律会自己溜出来,在我的脑海里轻轻播放。我不去跟唱,只是静静地听着,像看望一个沉睡的老朋友。然后,翻个身,继续面对第二天清晨的闹钟。
一生有你。终究,这只是一句歌词罢了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人美经典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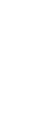 人美经典文章
人美经典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13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06)
2想和他一起去海边散步看星星阅读 (100)
3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98)
4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96)
5他曾说会包容我,后来对我处处指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