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石头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在那儿的呢?仔细想想,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起点。它不是轰然落下,而是一点一点,像河底的泥沙,随着年月,慢慢沉淀,最终变得坚硬、顽固。
我的父亲,是个石匠。这话说出来,好像带着点旧时代手艺人的浪漫,但其实不是。他的世界,是由青石、麻石、铁凿和锤子组成的。他的双手,指节粗大,布满老茧和细碎的、愈合了又裂开的口子,摸上去,像砂纸一样糙。我小时候,最怕他用手碰我的脸,那种触感,会让我不自觉地缩一下脖子。他话极少,一天下来,除了必要的吩咐,比如“吃饭”、“去写作业”,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。家里总是安静的,只有傍晚时分,他从工坊回来,那沉重的、带着石粉味的脚步声,是唯一的响动。
我们家住在一个老院子里,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,有些年头了。院角就搭着他的工棚,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和工具。空气里,常年弥漫着一种石头被切割、被打磨后产生的,微凉而干燥的粉尘气味。那味道,仿佛也浸透了我们家的窗帘、桌椅,甚至饭碗。那是我童年最熟悉,也最想逃离的味道。
我和他之间,似乎也隔着一块石头。我考了第一名,兴冲冲地把奖状拿回家,他接过去,在手里展平,盯着看了半晌,眼神像是在端详一块石料的纹路,最后也只“嗯”一声,把它平平整整地压在玻璃板下,再无二话。我中学时打球摔断了胳膊,疼得龇牙咧嘴,母亲在一旁急得直掉眼泪。他风尘仆仆地赶来医院,额头上都是汗,站在病床前,嘴唇动了动,最终却只是伸出手,极其笨拙地、重重地按了一下我完好的那只肩膀。那一下,很沉,很有力,几乎让我踉跄。那一刻,我感觉他按过来的不是一只手,而是一块石头。关心是有的,我感觉得到,但那表达的方式,却如此生硬、硌人。
于是,我拼命读书,一心想要考到远方去。填报志愿时,我所有的选择,都离那个省份远远的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我像是打赢了一场胜仗。离家的前夜,母亲在灯下为我收拾行李,絮絮叨叨,说不完的叮嘱。父亲则一直待在工棚里,叮叮当当的,不知在敲打什么。很晚,他才进屋,把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递给我。我打开,是一方青石雕成的镇纸,打磨得异常光滑,形状是朴拙的、不规则的随形,只在中间,他用极其精细的工笔刀法,刻了一艘小小的、正在扬帆的船。
他没说“一路顺风”,也没说“照顾好自己”。他就那么站着,看着我,然后转身去洗漱了。我握着那块冰凉坚硬的石头,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。那艘帆船,刻得真好,每一片帆都鼓满了风,像是要挣脱这石头的束缚,奔向无尽的远方。可它终究,是石头做的。
大学,工作,我在遥远的城市扎根。电话每周打一次,永远是跟母亲聊,父亲偶尔接过去,也只是那句万年不变的“钱够不够花?不够就说。”我谈过几次恋爱,每一次,当感情需要向更深处迈进时,我总会莫名地怯懦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些细腻的、温存的情感。我的心里,好像也梗着那块石头,它让我说出的“爱”字,显得干巴巴的,毫无分量。我继承了父亲的沉默,却没能继承他那能将石头刻出帆船的、无声的表达。
前年秋天,母亲生了一场大病。我赶回老家,在医院里守了半个月。父亲明显地老了,背佝偻了些,头发白了大半。他依旧沉默,但那种沉默里,多了些慌乱和无措。他不再去工棚,每天就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,一动不动,像一尊开始风化的石像。只有母亲喊疼或者需要翻身时,他会立刻弹起来,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极其小心,甚至有些颤抖地,去帮母亲调整姿势。那时我才恍然,他一生与石头角力,练就了一身的硬力气,此刻,却怕这力气,会碰碎了他生命里唯一的柔软。
母亲出院后,身体大不如前。我处理完工作,请了长假在家陪他们。家里的气氛,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那种石头般的冷硬,在疾病的冲击下,仿佛裂开了一些缝隙。
一天下午,阳光很好,我把藤椅搬到院子里,扶着母亲坐下晒太阳。父亲也在,坐在一旁的小凳上,默默地削着苹果。苹果皮从他指间垂下来,连绵不断,薄得像一层纸。母亲眯着眼,看着院角那落满灰尘的工棚,忽然很轻地笑了一下,对我说:“你爸啊,就是个闷葫芦。你刚出生那会儿,他抱着你,像捧着一块豆腐,动都不敢动。后来,他偷偷去选了块最好的青石,说要给你雕个长命锁。结果,雕了磨,磨了又雕,总是不满意,怕边角太利,划着你;又怕形状不好,硌着你。折腾了半年多,最后还是放弃了,给你买了把银的。”
我怔住了,猛地转头看向父亲。他削苹果的手停了一下,头埋得更低,耳根却有些发红。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把削好的苹果,仔细切成小块,放在碗里,递给母亲。
那一刻,我胸口那块压了三十多年的石头,仿佛被一种巨大的、温暖的力量猛地击中了。没有碎裂,而是开始剧烈地震颤,那坚硬的、冰冷的表层,簌簌地落下许多碎屑来。
我走到那间熟悉的工棚前,推开门,灰尘在阳光里飞舞。我在一堆废弃的石料里翻找,终于,在一个角落,我找到了它。那块被放弃的青石长命锁。它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,边缘都被耐心地打磨得无比圆润、光滑,握在手里,是一种温凉的、沉实的触感。因为打磨的次数太多,石面呈现出一种类似玉质的、内敛的光泽。它没有完成,但它所倾注的,是一个笨拙的父亲,对他新生的儿子,全部的无从开口的、近乎惶恐的爱。
我握着那块未完成的长命锁,走到院子里,在父亲身边坐下。他抬起头,看了看我手里的石头,又迅速移开了目光,神情里,有一丝被看穿秘密的窘迫。
我没有说话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些“我爱你”、“我懂你”、“辛苦了”,此刻都显得那么轻飘,那么不合时宜。我只是把那只未完成的石锁,紧紧攥在手心,感受着那份独特的、属于父亲的重量和温度。
夕阳西下,金色的光晕笼罩着我们三个人的身影。母亲在藤椅上睡着了,呼吸均匀。父亲依旧沉默地坐在那里,像一块守护着家园的、古老的石头。而我,第一次觉得,这块压在我心口多年的石头,它硌得我不再那么生疼了。它沉,依旧很沉,但那重量里,开始有了确切的、可以触摸的形状。
那是家的形状。是父亲用他一生的沉默,为我打磨出的,最笨拙,也最坚固的基石。爱,原来从未缺席,它只是像石头一样,沉默地存在于那里,等着有一天,我终于能读懂,那坚硬之下,所包裹的,最柔软的内核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人美经典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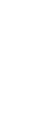 人美经典文章
人美经典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13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05)
2想和他一起去海边散步看星星阅读 (100)
3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98)
4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95)
5他曾说会包容我,后来对我处处指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