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是最让我心酸的。四卷本,封面是那种深蓝色的布纹纸,现在已经磨损得泛白了。翻开第一卷,扉页上有他清秀的字迹:“购于一九八五年春,于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。”那一年,他刚二十出头,和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。书里到处都是他年轻时激动的批注。在克利斯朵夫呐喊“要呼吸,要活下去,要战斗!”的段落旁边,他用钢笔狠狠地写着:“吾之写照!”力透纸背。我能想象,在那个春寒料峭的下午,一个穿着洗得发白中山装的青年,如何从紧巴巴的生活费里挤出钱,买下这套精神食粮,然后抱着它,像抱着一个滚烫的理想,穿过校园,心里充满了对广阔世界的渴望,以及征服一切的豪情。那时的他,笔下是汹涌的,是不顾一切的,是相信光凭一腔热血就能撞开命运之门的。
可是,当我翻开第四卷的末尾,那些批注的笔迹完全变了。不再是澎湃的钢笔字,而是用铅笔写的,淡淡的,带着一种中年人的审慎与疲惫。在写到老年克利斯朵夫变得平和,与命运和解的句子旁,他只轻轻地划了一道线,旁边是两个小字:“懂了。”没有感叹号,没有任何情绪的波澜,就只是“懂了”。这两个字,像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,从一九八五年一路飘来,落在我二〇二三年的手心里,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这套书,完整地记录了他从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,从“我要战斗”的激昂,到“我懂了”的沉默。这其间的二十年,他经历了什么?是事业的瓶颈,是家庭的重担,还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悄然褪色?他没有说,书替他记住了。
在书架的中层,有一本特别旧,特别破的《诗经》。它不是那种精美的收藏本,就是最普通的、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的版本。但这本书,大概是整个书架上最“富有”的一本。里面夹着的东西,简直像一个小型家庭档案馆。有他和我母亲恋爱时,互相传递的小纸条,压在《关雎》那一页;有我出生时,他用颤抖的手记下的体重和时间,写在《蓼莪》的空白处,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、不成形的脚丫;还有我上小学第一天,掉的第一颗乳牙,被他用纸巾小心包好,夹在了里面。这本书,早已超越了它作为诗歌总集的意义。它是一本日记,一部家庭史,一个父亲把所有最柔软、最珍贵的记忆,都安放在了这些古老的诗歌旁边。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,所谓文化,所谓传承,并不总是那些宏大的道理,它就藏在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的悸动里,藏在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”的感恩里,藏在一颗小小的乳牙里。
当然,书架上不全是温情。那几本厚厚的、关于西方哲学史和经济学的书,就带着一丝冷峻和疏离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是我青春期,和他关系最紧张的那几年。我觉得他古板,不理解我的世界;他觉得我叛逆,不脚踏实地。我们常常争吵,为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。那时,他不再和我讲道理,而是沉默地转过身,从书架上取下哈耶克或者萨特,默默地读。那些书里,几乎没有批注,只有一些代表着重读的折痕。现在我才明白,那不是他放弃与我沟通,而是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,寻找一个能安放困惑和失望的角落。他是在用先贤的智慧,来安抚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无力感。
书架的最底层,是一些关于植物和图鉴的书。这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。里面的批注又变得具体而充满生活气息。在银杏的图片旁,他会写:“小区南门第三棵,秋色最美。”在一朵兰花的素描旁,他记着:“浇水忌多,喜散射光。”他的世界,仿佛从一个浩瀚无边的精神宇宙,慢慢地收敛,最终落脚到了窗前的一盆花,楼下的一棵树。他从一个想要征服世界的青年,变成了一个细心观察一片叶子脉络的老人。这种回归,不是退缩,或许是一种更深刻的理解。他明白了,所有高远的理想,最终都要在具体而微的生活里找到它们的锚点。
如今,我每天都会在这个书架前站一会儿。我不再急于去读完某一本书,我只是静静地看。看着这些高低不齐、新旧不一的书脊,就像看着他一生走过的路。那些激昂的、温柔的、困惑的、平静的瞬间,全都凝固在这里,沉默如谜,又震耳欲聋。
他没有给我留下万贯家财,也没有留下一句成文的遗嘱。但这面书架,就是他留给我的全部。它告诉我,人应该如何热烈地活,如何温柔地爱,如何与困惑共处,最终,又如何与平凡的自己和解。他的一生,他所有的智慧与情感,都浓缩于此。
我伸出手,指尖轻轻划过那些熟悉的书脊,就像小时候,他牵着我的手,走过一条条陌生的街道。现在,轮到我了。我会从这里拿起第一本书,沿着他留下的足迹,慢慢地,认真地,读下去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人美经典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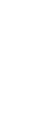 人美经典文章
人美经典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1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05)
2想和他一起去海边散步看星星阅读 (100)
3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98)
4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94)
5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