院子里的老枣树还在,只是比我记忆里粗壮了许多。树皮皴裂,像老人手背上的筋络。我记得小时候,一到秋天,父亲就拿着长竹竿打枣,红枣噼里啪啦砸下来,我在树下欢叫着跑来跑去,用衣襟兜住那些甜蜜的“炮弹”。母亲总是系着那条蓝布围裙,在树下捡拾,说:“轻点,别把枣子摔烂了。”此刻,树荫浓密,地上却干干净净,没有一颗落果。树下摆了一套我从未见过的石桌石凳,打磨得光滑,泛着冷冷的光。
“这树结的枣子还甜吗?”我尽量让语气显得随意。
“甜,特别甜。”他热情地回应,“每年都结好多,吃不完,邻居们都来摘。”他指了指石桌,“夏天在这儿喝茶,特别凉快。”
我点点头,没再说话。心里却想着,母亲以前总把吃不完的枣子晒成干,或者醉成醉枣,封在坛子里,等我过年回家吃。那醉枣的滋味,是带着酒香的、发酵过的甘醇,比鲜枣更醇厚,也更牵肠挂肚。
屋里的格局完全变了。原来进门是客厅,靠墙摆着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沙发,沙发对面是父亲的老式书架,塞满了他的工具书和我的课本。现在,客厅和旁边的卧室打通了,成了一个宽敞的开放式空间。墙壁刷成了时下流行的浅灰色,地上铺着光洁的瓷砖,吊灯造型别致,散发着柔和的黄光。一组线条简洁的灰色布艺沙发取代了旧物,前面是一张很大的原木色茶几。
我下意识地看向东面那面墙。那里曾经有一道铅笔画的、逐年升高的身高线,旁边还标记着日期。从“小豆丁”到“傻大个”,我的成长痕迹就刻在那里。现在,那面墙挂着了一幅巨大的抽象画,色彩斑斓,线条奔放,我看不懂,只觉得它堵住了我所有关于过去的视线。
“装修了一下,”他见我打量,便解释道,“以前的布局太老了,采光也不好。”
“嗯,现在这样挺好,亮堂。”我附和着,喉咙有些发紧。我记得那面墙旁边,原来还有个五斗橱,橱上放着一台笨重的老式电视机。多少个夜晚,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沙发里,看着雪花点很多的频道,讨论着剧情,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。那种属于家的、安稳的嘈杂声,此刻被房间里的寂静衬托得震耳欲聋。
他引我到沙发坐下,去厨房倒水。我趁机仔细环顾。阳台封起来了,做成了一个小茶室,摆着茶海和蒲团。那里原本是母亲的花园,她种满了茉莉、月季和死不了花,一年四季,总有或浓或淡的香气飘进来。夏天夜晚,我们会在阳台乘凉,我躺在凉席上数星星,父亲摇着蒲扇,为我驱赶蚊虫,也扇来夏夜清凉的梦。
他端来两杯水,是精致的玻璃杯,里面泡着柠檬片和薄荷叶。我接过,道了谢。杯壁传来的温热,恰到好处,却暖不了我突然觉得有些发凉的手指。我想起家里的搪瓷缸子,掉了瓷,露出黑黑的铁锈,父亲总是用它泡浓茶,茶垢积了厚厚一层。母亲常说刷不干净了,父亲却总笑着说:“茶垢越厚,茶越香。”
“这房子……您搬进来多久了?”我抿了口水,问道。
“快五年了。”他说,“当时看中这个地段,生活方便。虽然房子旧点,但格局方正,改造空间大。”
五年。我心里默算着。我们搬走,也正好是五年。父亲退休后,执意要回老家养老,说城里的空气没有泥土味。卖掉这房子的那天,母亲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哭了很久,她摩挲着那道身高线,最后还是父亲叹了口气,用一块湿抹布,一点点把它擦掉了。我当时站在旁边,看着那模糊的铅笔印迹,感觉像看着自己的根被硬生生从泥土里拔起。
“之前……住这里的那家人,听说也是老住户了。”我试探着问,装作不经意。
“好像是吧,”他想了想,“听中介提过一嘴,说是一对老夫妻,住了几十年。我们买的是二手房,手续办得挺顺利。”他的语气平常,就像在谈论一件普通的商品交易。他当然不会知道,他口中那对“老夫妻”,是我的整个世界。他也不会知道,这个他精心改造的、充满现代气息的空间,埋葬了我整个喧闹又温情的少年时代。
我起身,说想去洗手间。他指了指方向。洗手间也彻底变了样,干湿分离,智能马桶,恒温花洒。雪白的瓷砖一尘不染,散发着消毒液的味道。我关上门,背靠着冰凉的木门,深深吸了口气。这里,曾经有一个老旧的浴缸,我小时候总是在里面扑腾,弄得满地是水。墙壁上贴着卡通图案的瓷砖,有一块小熊的,被我磕掉了一个角。镜柜里,曾塞满了母亲的雪花膏和父亲的剃须刀。而现在,这里干净、整洁、功能齐全,却也陌生得像任何一家高级酒店的客房。
走出来,他正站在窗边打电话,语气温和地交代着工作上的事。我看着他挺拔的背影,与这个崭新的环境如此和谐。他是一个合格的主人,热情、周到,把我当作一位普通的客人招待。而我只是一个闯入者,一个来自过去的、格格不入的幽灵,在这个熟悉的坐标上,寻找着早已消失的坐标点。
我忽然明白了那句“那是我家”的真正含义。那不仅仅是指这处房产的归属,更是一种宣告——宣告着现在,宣告着他对这个空间的绝对主权和重新定义。而我的“家”,早已随着父母的离去,随着那些旧家什,随着墙上的身高线和阳台上的花香,消散在时光里了。它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,像一部褪色的老电影,无法重映,也无法被这个现实的空间所容纳。
我没有再久坐,喝完那杯水,便起身告辞。他送我到了门口,依旧客气地说:“有空常来坐。”
我笑着点点头,没有应承。我知道,我不会再“常来”了。走下台阶,回头望去,那栋楼,那个窗口,在夕阳下和周围的建筑没有任何区别。它只是千千万万住宅中的一套,有一个新的主人,一段新的生活。
风吹过,老枣树的叶子沙沙作响。它见证了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,却沉默不语。我转过身,沿着来路慢慢走去。心里那片曾经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,此刻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填满——有物是人非的怅惘,有对往昔的深切怀念,也有一种释然。或许,每个远行的人,最终都要学会与记忆中的那个“家”温柔地告别。它不曾真正消失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安放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供我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,反复回味,取暖前行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人美经典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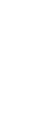 人美经典文章
人美经典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14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07)
2想和他一起去海边散步看星星阅读 (100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0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98)
5他曾说会包容我,后来对我处处指责